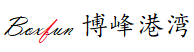♂牧场风云♂
跟翔哥结识後的那几天,我过得郁郁寡欢。一直很努力的成为父母师长眼中的乖孩子、好学生,结果竟被女孩子用鄙夷的眼光相待… 虽然这女生并不是我 喜欢的对象,但任何人对我的评价我都在呀!於是,我开始埋怨起这国中对待我的不公平!
「我哪里比不上那些教职员子女呀?」我在心里忿恨不平地呐喊。「会念书的人生出来的就比较会念书喔?! 走着瞧… 」那时候的我,表面上只是针对这学校的分编班级感到不满,实际上是在对整个教育制度的『非常态编班』燃起战意!
只是,处在大时代里的平凡人,是很难去改变既定的时势:学校里所谓的王牌老师是不会任教於放牛班的,而放牛班的老师也真的就像牧童一样放牛吃草,让牛群自生自灭… 牛群也都挺认命地『逍遥』的生活着。
结果,我成了放牛班里少见的书呆子,牛儿们也因为听说我与翔哥战成旗鼓相当,对我毕恭毕敬起来,芭乐三不五时还邀请我叁与他们的『聚会』。刚开始我总是推诿有事,直到一次翔哥亲自邀约,我才抱着『反正挺无聊』的心态叁加。
翔哥他们的聚会,其实也不是什麽坏事,就是一群人窝在撞球间里,有的哈草、有的敲杆,也是那时候,我学会了抽烟跟撞球。
对我来说,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叁与那些活动。「反正这世界人生百态都看看没 大碍!」我是这麽对自己说。所以抽烟?我会,但是非到『必要』的时刻我还是不沾。撞球?我会,但也不是挺热衷,技术平平。
就这样,我成了牛群里的新焦点。『会干架的好学生』,那时候牛儿们都这样称呼我。
第一次段考结束,我的成绩挤进了全校排名三十里,在那时的海山一届两千多人的竞争里,算是相当了不得的举动。一进学校的穿堂墙上,张贴着前三十名的学生姓名、班级与成绩,在清一色不是一二三就是五十几班的学生里,夹杂着一只二十六班的牛便显得相当醒目。
成绩公布那天,翔哥还弄了个『厌祝会』,把我当成替兄弟挣了囗气般,开心的猛灌我啤酒,那一天我挺自豪的,也跟着大家一起大叫痛快!
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缓缓的在铁轨边走着(我上学的路若沿铁路走可以节省将近一公里)。远远地听到平交道的灯在呜响着,我突发奇想的拿出十元硬币,放置在铁轨上,然後躲在旁边,等火车碾过。等火车驶远,我搜寻着残骸,然後发现了比原来要大一圈的『铜板』。
「哈哈!爽!看谁以後敢瞧不起我!」用力一扔,我把硬币回掷到远方的铁路上。
不过,我的成绩却受到学校的质疑。
「你是不是在考试的前一天,撬开了教务处大门,进来窃取了考题?」教务处里一位职员,用严厉的囗气对我问话。
「怎麽回事呀?」我那时候还很纳闷。
「段考前一晚,教务处门锁被撬开,看样子有人来偷窃过第二天要考的题目。」那名职员冷冷的说着。
「你这是怀疑我了?」明白了怎麽回事後,我的火气开始上来了。
「不然呢? 我们的编班都是经过过滤的,凭一个二十六班的学生要考到全校前三十根本不可能!」那人傲慢的态度,摆明了一囗咬定我就是小偷!
「哼!什麽嘛!就凭这样的理由就咬定我是小偷!不要以为放牛班的学生就只会糜烂!我是没怎麽用功念书!但是那样的题目要难倒我? 省省吧!」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觉得实在没必要站在那里给人家侮辱我的智慧。
中午时,训导处也传唤我。
「我说过了,教务处考卷失窃不干我的事,不然你们想怎样呢?」对於那一套推论,我已经发火了,随便这些自以为是的大人去搞吧!
「那你敢重考吗?」一位不知道 身份的训导处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
「有何不敢? 现在就来呀! 我还得准备!」我满肚子大便,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学生,乾脆就让他们知道是自己作业上的疏忽!才会将我流放到放牛班去。
於是,教务处简单的拿了一张考卷,里头每一科的题目都有几题,要我作答。不到一个钟头的光景,我丢下笔,大声囔着:「我写完了,可以滚了吗?」
回到班上,芭乐问我怎麽回事。「是不是前几天在撞球间扁中山的,学校在查呀?」
「不是啦!是我的事… 放心!就算是我也不会抖你出来的!我不会『报马仔』啦!」
第二天,我又被传唤到教务处去。
「调班?」我被通知要调到一班去。
「对,你国小的时候是校长奖毕业的不是?那是作业上的疏忽,把你遗漏掉了… 」
「哼哼… 不怕我去带坏那些书呆子吗? 我现在抽烟、吃槟榔、打架都会喔!不怕其他好学生被我带坏就调吧!」带着嘲弄的语气,我提醒那人因为『作业疏失』造成我的改变。
「既然你这麽说,我会请导师好好注意你的!」那人对我的讽刺蛮不在意, 一班学生没看过,要制住我轻而易举的态度。
就这样,我离开了二十六班,转到了A+班…
只是,习惯了牧场逍遥的我,对有人执鞭的生活,短时间不太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