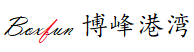虽然厕所就在院角,而且是男女分开的,但是大舅姥爷还是按照他一贯的做法,转过身就到墙根尿了起来。他就是这样,当着我和我妈妈的面也是如此。我只好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我几乎从来没有正视过大舅姥爷,因为他老人家的裤子大门永远是大开着的,谁说也没有用。
他尿完后,又回到桌子边坐下,喝了一口酒,对我爸爸说:
“小明,想不到老家还是不行,你这还稍微好一点,你看小光家,连个彩电都没有。要是我来当村长早就带着大家奔小康了。”
爸爸笑笑说:
“乡下就这样,小光也很不容易,在农村开裁缝店忙的要死还挣不了多少钱。”
二舅姥爷说:
“我不知道小光看的黑白电视机,不然我这次来就给他带一台。我们上海人搬家彩电冰箱还有的把空调都扔掉了。”
大舅姥爷马上说:
“有的人搬家连小汽车都扔掉了。”
我听的很别扭,前两年他们在我家吹过类似的牛皮,我当时少不更事,笑嘻嘻地问他们,二舅姥爷,你家扔了多少空调?然后又问大舅姥爷扔了几台汽车?是不是玩具汽车?谁知道我刚说完爸爸抬手就抡了我一巴掌,当时就把我打蒙了,为这我妈妈和我爸爸闹了好长时间的矛盾,差点把离婚都提上议事日程。
这回我学乖了,爱怎么吹就怎么吹去。
大姨奶奶不屑地说:
“你们两个吹起牛来倒真像亲兄弟。你们在上海是个什么样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大姐夫官当的也不算小了,现在退休工资一个月就2800,我们就从来不在外头吹。”
大舅姥爷说:
“你有钱咋了?我们也不是没见过钱。”
二舅姥爷也在符合着。
大姨奶奶较起真来,大声说:
“是吗?既然这样,这次立碑的钱咱们三个人平摊。你们都是当儿子的,凭什么要我这个做女儿的立碑?你们不觉得没面子?”
这下,两兄弟都不干了。
二舅姥爷说:
“大姐,立碑是你提出来的,本来我是不打算来的。可是,如果我做儿子的不来,你也没有面子。你既然有钱那你就出嘛,我们捧个场来回也是有花销的。”
大舅姥爷说:
“对嘛,特别我这个当长子的更要来了。我年轻时给这个家出了多少力,咱爹死的早,咱娘买那个木板房当时是75块钱,大头都是我出的。你才出了几块钱?我出力的时候已经过了,现在老娘死了这么多年了你立个碑有什么亏的?”
二舅姥爷话里有话地说:
“是啊,大哥出力最多,谁比得上大哥?”
大姨奶奶果然上当了,冲着大舅姥爷说:
“你真好意思说你的贡献大,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别人不知道你自己还不知道?成天就认你的老酒瓶子,见了酒比见了你爹还亲。咱娘活着时你给咱娘多少钱?你管过多少?”
大舅姥爷不服气地说:
“管不管也比你管的多,你在北京还能比我在上海管的多?”
大姨奶奶说:“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咱娘临死之前不是到北京住了一年多,你接咱娘回上海的。怎么回去几个月就死了?你说?”
大舅姥爷开始愤怒了,挥着手说:
“咱娘在北京怎么了?咱娘在北京呆了一年多,哪个月的退休工资都一分不少的给你寄去,晚寄几天你都打电话来闹。咱娘都80多了,能用多少钱?你立碑咋了?你立个碑也不吃亏,你以为你多孝顺?”
二舅姥爷笑眯眯的一手搂着旺旺,一手拿着一支烟,饶有兴致地观看着。
我爸爸极力地劝说,但无济于事。
大姨奶奶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愤怒而涨的通红。指着大舅姥爷说:
“建功,你的意思是我赚沾咱娘的光了?咱娘在上海时间最长,谁沾咱娘的光了谁清楚。我18岁就嫁人了,我没靠过咱娘,哪个不要脸的靠咱娘自己清楚。”
大舅姥爷看了一眼二舅姥爷,恶狠狠地说:
“说的对,谁知道哪个不要脸的畜生沾咱娘的光。”
二舅姥爷马上反应强烈地对大舅姥爷说:
“你什么意思?你骂谁?”
大舅姥爷没好气地说:
“你心虚什么?谁心虚就是谁。”
于是,弟兄两个又舞动老拳,拉开了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