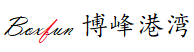原来女孩子喝醉了也这么难伺候!
顾蕾一路挣扎着自己上楼,东倒西歪地却不肯让我扶.我很怕她会摔倒,小心翼翼地跟着她来到房门前.她伸手去兜里摸出钥匙,嘴里含混不清的叨咕着:"你…可以回去了,再…再见."我当然想再见,问题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钥匙准确地插进钥匙孔,令我难以忍心说再见.
我抢过钥匙,把门打开.她踉跄着走进卧室,一头载倒在床上.我犹疑了一下,跟了进去.卧室不大,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她要双人床干什么?我替她把那双漂亮的黑色短靴脱下,握着她纤细的足踝时,心里居然跳得厉害.
她在床上翻了个身,用一种这个星球上没有的语言说了句什么,沉沉睡去了.
我不急着走了,坐下点燃一根烟,静静地倾听她细长而均匀的呼吸声,欣赏着她甜美而安详的睡态.她的脸被酒气蒸得泛出桃花般地粉红色,胸前高耸的一双优美的弧线随着呼吸有节律的一起一伏,滑到膝盖处的长裙暴露出一截雪白如嫩藕似的小腿,我内心蓦地涌起一丝冲动.
我几乎无法抑制这丝冲动.在我短短的生命中,曾经多次面临这种冲动,曾经被它摧残折磨得难以自持,曾经被它牵引着跨越过人生痛苦与快乐的极致.我忽然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从前的女友,多少难忘而痴醉的夜晚已随风而逝,今天的她是否也可以象这样沉稳而舒心的睡去,异域的夜色是否也如这里般浓重而澄静,陪伴在她身边的会不会是她的一位我可能终身难以谋面的温柔知己,我祈祷上苍但愿分手时那些冲动的话语不会在她心中烙下痛苦的印记.
我起身来到卫生间,把灼热的大脑浸在凉水中冷却.卧室中的她叫了一个人的名字,无法听清是谁.我返身回到卧室,替她盖上一袭薄被,然后悄然离去.
我来到办公室时,老周一如往常地埋头在报纸堆中,但我可以察觉到一丝不同往常的肃杀之气.
第一个来电话的是老强.老强调侃地问起昨晚的情形,我回答说一切都按预想的发展了--该发生的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没发生.老强在电话那头发出会心的笑声,说:"请客!"我说:"改天吧."老强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第二个来电话的是刘姨.刘姨说帮我约好了一个姑娘,要我去见见,我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刘姨大吃一惊,说"这么快,太好了,什么时候领来到我家吃饭,让我帮你看看."我说:"改天吧."刘姨满怀憧憬地挂断电话.
第三个电话是顾蕾来的,顾蕾在电话里异乎寻常的冷淡.
"昨天很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她客气地说."没什么,我不是也麻烦过你."我说.她接着念了一串数字,说:"这是思真的电话,你记一下吧,她明天就回来了."我拿笔记下,说:"谢谢."然后她就收了线.
她的这种态度多少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预料她对我有点什么,事实上看起来她对我根本没有什么,我颇有些失望,安慰自己说: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天上的云彩变得快,忽冷忽热的.我到底希望不希望她对我有点什么,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科长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拍了拍我的肩说:"小蒋你来一下."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顺从地起身跟了出去.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有一种目送革命英雄奔赴刑场的壮烈.
来到吸烟室,点上烟,科长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匿名给局党委写了封检举信,在安华公司的引进项目上大作文章,你知道这件事吗?"说完定睛看着我,静待我的反应.
我着实吃了一惊.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人率先发难.虽然我同这封检举信没有丝毫瓜葛,但是我为有人敢于仗义执言而感到由衷的欢欣鼓舞.从科长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很疑心这封信是我的作品,我有必要打消他的这种疑虑吗?既然我为有这样一封信而欢欣鼓舞,那么这封信是不是我写的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的脸色从最初的惊悚很快转为平和,淡淡地答道:"我不知道."
科长并不相信我的回答,他盯着我沉默了良久,然后说:"这个项目的调查报告是你写的,局党委最近可能会找你谈话,我希望你能摆正态度,实事求是."他在说"实事求是"四个字的时候明显加重了语气.我不由觉得好笑,也就笑着回答:"我一定摆正态度,实事求是."我在说"实事求是"时也加重了语气.
科长感到失望.科长掐灭了烟蒂,说:"顾局长对你在调查报告中的见解很感兴趣,他今天晚上要请你去他家里吃饭."
我愣住了.
对于一个机关里出身平凡的小公务员来说,局长的邀请无疑是极具魅力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我可以清醒地意识到它背后所隐伏的动机,称它为鸿门宴绝不为过.
我忽然有点可怜起这位局长来,高高在上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屈尊向一个他的不起眼的下属发出这样的邀请,这种有点抛媚眼性质的邀请本身就足以说明如今他的处境维艰.高处不胜寒,他的劣势在于他无法失去今天手中把握的一切,而我则无所谓.我本来就一无所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不害怕失去什么,这使我可以在危机面前保存自己的尊严,虽然这种尊严在他们眼里可能贱如草履!
我微笑着回答:"对不起,今晚我没空."
科长的吃惊在我的意料之中,对于他们来讲,拒绝这样的邀请象一个草民拒绝黄袍加身一样不可思议.他张大了嘴,愕然地盯着我的脸,过了半晌才怔怔地说:"你想清楚了,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我拿自己的前途开了一个大玩笑.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去一个偏远山村调查当地农机的普及情况,我欣然从命.一边的老周忿忿然地说:"怎么搞的?不说派辆车送你去,也没提那边有没有人接待."我安慰他:"我年轻,坐火车去也没什么不好,没人接待不是更利于我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么."老周叹了口气,说:"年轻人,好好保重,那地方穷山恶水的,可有苦头吃了."我被老周的关心所感动,回报了一个真挚的微笑.
我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山沟里盘桓了半个月,夜半独坐山头抽闷烟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拂不去思真俏丽的身影,偶尔也会想起顾蕾,这两个女孩的存在使我异常留恋大都市的繁华和喧嚣.
半个月后我终于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了繁华而喧嚣的都市.
上班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拨通了思真的电话,思真对于我的突然出现显然没有准备,她在问清了我的名字后迟疑地问:"你找我有事?"我极度沮丧,看来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几乎使她在脑海中完全淡漠了那个当初贸然请她看电影的男孩的形象,我提醒她:"我们曾经两度邂逅,一次在电影院,另一次在一家书店,那次你是要去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顾蕾."这个名字刺激了她的记忆,她有些热情起来:"是啊,听顾蕾说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去她家里找我,吐得满地都是,你可真有意思."
我的确挺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电话打得更有意思,人家姑娘把你忘得差不多了,你却还来打扰人家,会不会算是恬不知耻?我思考了一分钟,觉得要对自己半个月的魂牵梦萦有个交代,于是硬着头皮说:"思真,我想请你吃饭,你不会拒绝吧?"
思真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半晌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条件是要带上顾蕾--林妹妹身边为什么总要有个宝姐姐?我妥协了.
思真和顾蕾坐在了我的对面.这是一家离我宿舍不远的小店,这种大排挡似的小店令顾蕾有些不满,她说:"啊,就在这么寒酸的地方请我们呀?"我很想骂:你臭摆什么小姐架子成心拆我的台呀,话到嘴边儿发生了变化:"这儿人少清净,说话方便,有什么不好?"
幸好思真似乎并不挑剔这儿的环境.点过菜后,她轻声细语地问:"今天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请我们吃饭呢?"
我大窘,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暗忖:你思真是真不明白呢还是假装糊涂?一个男孩约一个女孩吃饭还能为什么事?难道还能是专程找你探讨北约东扩或者海峡危机?可是我羞于明言,总不能说我曾经受过你的暗示,觉得你对我有点意思,所以借着吃饭向你示爱吧?况且人家给过你什么暗示?写在脑门儿上了?万一是你自我感觉良好呢?再说即便有暗示也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了,难道暗示不会过期?密封罐装的酱菜都能过期,凭什么暗示不会过期?
正当我苦心孤诣地想编造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时,顾蕾插话了,顾蕾说:"这还用问,他喜欢你,想见你呗!"